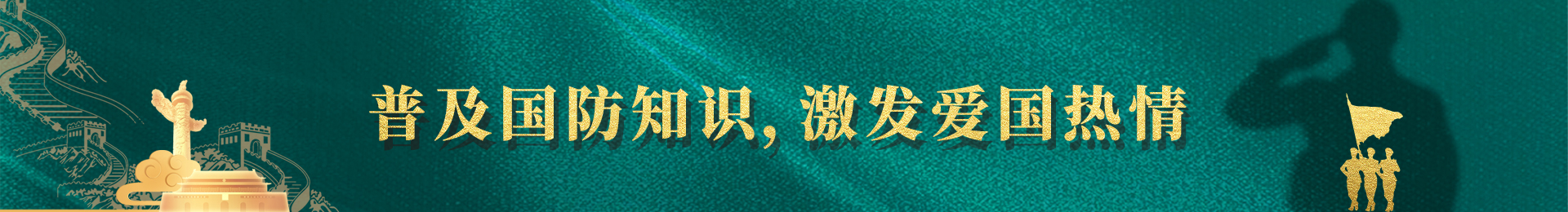协会地址:苏州市虎丘路88号

马军武喜获全国道德模范奖

马军武夫妇在哨所旁开垦的菜园喜获丰收。

夏季蚊虫肆虐,每次外出检查边境设施,马军武夫妇都用沾油的纱布遮住脸。

严冬时节马军武夫妇巡逻在边防线上。

清晨,马军武夫妇升国旗,敬军礼。 【主人公简介】马军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一八五团桑德克民兵哨所护边员。1969年出生,共产党员,1988年9月担任护边员,24年如一日坚守在边境,先后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兰州军区优秀护边员等荣誉。 那场洪水让我走进了桑德克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二代子女。我的父亲从山东莱西入伍进疆,后来就地退伍。我母亲随父亲支边,一起留在了新疆。我从小生长在一八五团所在的中哈边境地区,目睹了父辈们在戈壁滩上艰苦创业的日日夜夜。 1988年4月23日,位于边境内的阿拉克别克界河突然发生特大洪水,水势凶猛,势不可挡。那一刻,全团干部职工心里都清楚:界河我方一侧地势低洼,洪水一旦不能及时控制,全团家业就要毁于一旦。更严重的是按照国际法惯例,如果任凭洪水肆虐,以河为界的原河道就会被洪水淹没,改道流向我方,会使包括团机关在内的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他国领土。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土受损!”在团领导的率领下,全团男女老少齐上阵,用沙袋筑河堤、挖应急引导渠,经过16个昼夜的围追堵截,终于将洪水引回了原河道,保住了险些丢失的家园。 打那以后,团里深深意识到预警的重要性,决定在桑德克地区的界河边上设个民兵哨所,派专人到那里担负护边查水任务。 那时,我初中毕业在团里种地、打渔,正觉得没啥意思。听到这个消息,我动了心。那天吃晚饭时,我试探父亲:“团里在桑德克设哨所,我想去!”父亲一愣,马上反问我:“你想好了吗?那可是一个人的哨所,吃喝拉撒睡都得靠自己,你行吗?”我知道,在父亲的眼里,我依然是个孩子,担心再正常不过了。“走不出家门,我永远也长不大,我想去锻炼锻炼!”父亲看我决心很大,就笑了:“先去试试,顶不住了我去换你!”父亲的一句玩笑话,让我信心倍增。 第二天,我找到团武装部领导,表明了自己要去桑德克哨所的决心。领导看我态度诚恳,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 1988年9月20日,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上起来,吃过母亲给我做的送行饺子,背起装满生活用品的麻包,我正准备出门,母亲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紧紧搂住我的胳膊说:“儿子,你一个人去,妈不放心!听说边境上经常有狼群出没,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妈怎么活啊!”父亲是个机智的人,看到这种僵局,他马上从墙上摘下我家那杆早已锈迹斑斑的猎枪对我说:“带上这个,遇上野兽可以防身。”他的话让母亲缓缓松开了我的胳膊。 通往桑德克哨所没有路,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我沿着牧民们踩出的羊肠小道,一会儿踩着骆驼刺,一会儿穿过沙枣林,一会儿又翻越盐碱沟,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在走过一大片蒿草丛时,我被10多条毒蛇盯上了。这些很少见到人的家伙个个高昂着头,吐着长长的信子,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往左躲它们就往左移,我往右避它们也集体往右游动,一副随时致我于死地的架势。我害怕了,浑身毛骨悚然,汗也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突然想起老人们常说蛇怕烟熏的说法,我赶紧掏出火柴,就势点燃了脚下的蒿草。一阵烟熏火燎,所有的蛇瞬间都不见了。那一刻,我为自己的机智而得意。 20多公里路程,我竟整整走了一天。太阳落山时,我走进了桑德克哨所。天哪,这哪里是什么哨所——两间土坯房子,一个土灶,用石头和砖块搭起的台子上放着一块简易木床,一摇三晃,随时都可能塌掉。没水没菜,也没有米面,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好在我早有思想准备,万事开头难嘛!我从界河里提来一桶水,用3块石头支起带来的铁锅,下了一把挂面,算是吃了来桑德克哨所的第一顿饭。9月份的桑德克,气温稍有些低,躺在吱吱扭扭的木床上,我怎么也无法入睡。我知道,从现在起桑德克就是我的家了。 那面国旗又把我留在了桑德克 桑德克是哈萨克语,翻译过来就是“空箱子”的意思。我常自嘲:装在“空箱子”里的一个人,不就是个“囚”字嘛!没有想到,日复一日,我竟心甘情愿地在桑德克这个“空箱子”里“囚”了20多年。 哨所离中哈边境的界河不足10米。我的主要任务是巡逻,有时白天巡,有时晚上巡,方圆几十公里边境线,一圈巡下来足足得走10多个小时。除了高度警惕偷越国境的不法分子之外,大多数时间是要将牲畜和野兽破坏的铁丝网及时修补好。到了夏秋雨季来临时,我就连天连夜守在阿拉克别克界河边上,观察水位的变化。团里为了让我站得高看得远,用木头在界河边搭起一个高高的掺望塔,站在上面,附近的情况一目了然。 说实话,吃苦我不怕,巡逻走路我也不在乎,最难忍的是一个人闷着,没对象交流,孤独寂寞不说,连说话都迟钝了。有一天,我到防区南段巡逻,老远看到一个牛圈,我高兴坏了,心想,这回可找到人说说话了。谁知,一路小跑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废弃的牛圈,啥也没有。我好失望。 这样的日子仅过了半年,我熬不住了,心里不知不觉打起了退堂鼓。有一天下午,我趁回团部开会的机会,悄悄找到了武装部的刘玉生部长,我给他说不想干了。刘部长好像早有预感似的,笑着拉我坐下。他问我:“你听说过沈桂寿升国旗的事吗?”我说:“没有呀!”“那我讲给你听听!”说着,他从锁着的柜子里取出一面半新不旧的国旗摊在我面前,郑重地对我说:“这就是沈桂寿当年升起的那面国旗。”他告诉我,沈桂寿是一名上海知青,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来到我们一八五团屯垦戍边。1979年春季的一天,他和大伙们在边境线附近的地里干活,远远看见对面邻国的士兵正在升国旗,那股庄严劲儿令人羡慕。“我们也要升国旗!”说着,他就扔下手里的工具,跑到团部的商店买了些红布,回家连夜缝制了一面国旗。第二天,一根由长长的桦木杆撑起的国旗,在我边境庄稼地的上空高高升起。直到团部门前正式修建了国旗升降台,这面国旗才被收回珍藏至今。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从团部回来后,我也想在桑德克哨所升国旗。正当我积极筹备,找来石头、水泥和沙子砌升旗基座时,刘部长来了。想不到他竟然跟我不谋而合,给我带来一面崭新的国旗不说,还用钢管特制了一根旗杆,用车拉了过来。我兴奋极了,与刘部长一起动手,一会儿就把国旗升起在了哨所的上空。那一刻,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真的流泪了。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人,为祖国守防,那种责任感和光荣感一下子就涌遍了全身。当着国旗的面,我向部长表了态:“好好干,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赖!” 心情好了,干什么都带劲。我把巡逻时可能越境的地段一一标上记号,把洪水冲垮的河堤画在纸上,回到哨所后,借助煤油灯的亮光绘制出一份简易“防区图”,有了重点巡逻的一手资料。 因哨所的房间低矮,见不到阳光,我就找来玻璃板做成一个偌大的反光镜,将太阳光反射进来,让原本阴冷的屋子,一下子变得亮堂堂、暖烘烘的。哨所周围都是荒地,我把石头和杂草除掉,挑来水,开垦了3分多土地,种了一些花草和菜苗,既解决了吃菜难题,又美化了哨所的环境。我的主观能动性让哨所的生活一下子有了生机,自己也就不觉得烦闷了。 30本日志记下了我的桑德克生活 24年,8000多个日日夜夜,我的生活几乎每天如此:起床,升国旗,上掺望塔,巡逻。 登上掺望塔观察是我的基本工作,早中晚一天3次,雷打不动。遇上刮风下雨或者是冰雪天气,上下一次也很艰难。最早的那个掺望塔,是用木头搭建的,18米高,稳定性不好,人上下时咯吱咯吱响不说,风大时还摇晃得厉害,踩在上面总有一种随时要倒塌的感觉,挺吓人的。 2006年,团里怕出危险,弃用了旧的掺望塔,又在旁边用钢板建起一个30米高的新塔。这个塔稳定性极好,98级台阶虽然很陡,但爬起来过瘾。站在塔上不用望远镜,附近边境线的风吹草动尽收眼底。冬天结冰了,台阶非常滑,上下都得抓着扶手。有一次,我忘了戴手套,一把抓到钢管扶手上,活生生地扯下一层皮,伤口好长时间才愈合。 边防无小事,要做到万无一失,就得时刻睁大眼睛。为防止人畜偷越国境线,重点区域我天天都去看看。我用旧雨衣帽子缝制了一个 “百宝囊”,里面装有铁锤、钢钳、紧线器、铰棍等10多公斤重的工具,一旦发现铁丝网出了问题,随时补修。平时可以骑着摩托车巡逻,冬天大雪封路,只能徒步穿行。 桑德克地区三面环山,气候湿润,是贝母、人参和鹿茸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生长的好地方,也是不法分子偷猎盗药的集中地。一次在巡逻路上,3个陌生人向我问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发现了“情况”。晚上,我仔细研究过自制的“防区图”后,就在他们可能出现的地段潜伏下来。果然,深夜两点多钟,这3个人来了,竟然准备偷越国境。情况危急,我便大声呵斥起来,吓得3个人落荒而逃。当晚,我把情况报告给了当地派出所,民警紧急出动设卡盘查,很快就抓住了那3个人。问讯后才得知他们偷越出境为的是盗窃药材。 1999年的一个冬夜,我刚躺下,突然接到团部打来的电话,说接到举报,今晚有一名逃犯可能要从桑德克越境,上级命令我配合当地派出所守株待兔。我知道,当时大雪封路,逃犯要想越境只有靠近大路西侧的那个界碑处,其他地方雪深路窄,又是夜间,不可能过去。于是,我在界碑附近的山坳里掏了个雪窝,把自己隐蔽起来,双眼紧紧盯着大路的方向。雪窝子就是个冰洞,一会儿就把我的双脚冻麻木了,鼻子、眉毛上也很快结了厚厚一层白霜。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天亮也没发现情况。回到哨所才知道,逃犯凌晨两点多就被派出所抓住了,只是没法通知我。 虽然白白守了一夜,但我依然很高兴。我把这些事一件件记在工作日志里,让它成为桑德克边防和平与安宁的永久见证。20多年过去了,我数了数,一共记了30本日志。日志上不仅详细实录了我100多次处置险情的过程,还统计了我一共穿坏了600多双胶鞋,走了30余万公里的路,相当于绕地球7圈多的一些数据。没事时,我自己拿来读一读,仍然回味无穷。 我年年品尝着桑德克“四季”的味道 有人开玩笑说,在这里呆着,一年要“死”4次: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它的确印证了环境恶劣的事实。每到春季,桑德克的气温一回暖,山上的积雪就会迅速消融,不知何时就会汇成巨大的洪魔咆哮而下,那声势排山倒海,令人惧怕无比。所以,一到这个季节,我晚上都开着门窗睡觉。一方面是通过听水声来判断洪水的流量,另一方面一旦堤坝发生险情能及时冲出去应对。 记得那是200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界河突发洪水,从上游冲下来的朽木瞬间堵塞了河道。情急之下,我划着自制的皮筏子去疏通河道。突然一连串大浪打来,将我卷入洪水中。好在慌乱中我抱住了水中的一根粗木,被冲出去4公里多路,我仍然安然无恙。 桑德克的蚊子是出名的个大,毒性也极强。每年6月份一过,一种叫“小咬”的蚊蠓就会铺天盖地,头发里、耳朵里、甚至是鼻子里都无孔不入,咬起来疼痛难忍。那年,我父母为了给哨所增添点生活气息,托人给我捎来两条小狗和几只小鸡。没想到刚好赶上蚊蠓肆虐的季节,活蹦乱跳的小狗和小鸡活了不到10天,就经不住蚊蠓的叮咬,相继死去。这些年,我琢磨出一套防蚊蠓的办法。巡逻时,头上顶一块沾过柴油的纱布,虽然柴油刺激得脸和脖子上的皮肤火辣辣的疼,但蚊子不敢靠近。到了晚上,我把牛粪当作蚊香,点燃在屋子里驱赶蚊蠓,效果很好。但现在不用了,时间久了人有了免疫力,蚊蠓的叮咬也就不起作用了。 桑德克的秋季是最迷人的,阳光软软的,风也轻轻的,一片片金黄金黄的杨树林,远远望去,如同巨幅油画,让人看不够。 但这种好景色只有10多天,很快秋风挟着沙尘,吹着尖尖的口哨接踵而来。尤其是到了晚上,那无遮无挡的大风,狠劲拍打着我的土房子,好像要把房顶揭开。到了冬季,哨所就成了“雪海孤岛”,进不去、出不来。1米多深的积雪,零下30多摄氏度的气温,完全是一个冰的世界。之前,哨所没有电视,我就买几本书备着。等大雪把路封死了,我就开始读书。有时一本书能读三四遍,好多段落都能背下来。 2006年11月21日,是我最兴奋的日子。这天,团里为哨所接通了常明电,并安装了卫星电话和电视。尤其是那套被称之为电子“千里眼”的视频监控系统,不仅一下子解放了我的双腿,还让桑德克边境的安全从此又有了新的保障。 我的蜜月是在桑德克哨所度过的 1991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本团九连的姑娘张正美。经过一年多的恋爱,第二年10月,我们幸福地走进了婚姻殿堂。结婚当天,我租了辆轿车,把爱人接到了哨所。我们的蜜月是在桑德克度过的。 那阵子哨所的条件依然艰苦,为了讨新娘子欢心,我想了不少“馊点子”。买一大卷红纸,把那间土屋的墙围糊了一圈,为的是图个喜庆,也像个新家。我知道张正美喜欢小动物,就专门买了6只鸽子和一对兔子,养着逗她开心。刚开始她还新鲜了一阵子,半个月后就耐不住了,抹着眼泪央求要回娘家看父母。看着她那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只好放行。没想到,一走就是半个月不见人影。每次去接她回来时,她都要劝我:“军武,哨所哪像个家呀?咱们不在那里呆了,回团部好好过日子行吗?”每次我都骗她:“等团里选好人来接我站岗,咱们就回去。”没想到,一骗就骗了两年多。随着时间的磨合,张正美竟慢慢适应了哨所的生活,再不频繁地提及回娘家的事了,偶尔还能陪我去巡逻一次。 我知道夫妻间的幸福是经营出来的,有了彼此的信任和甜蜜,苦难就不算苦难了。我除了掺望和巡逻外,把对哨所之家的经营同样放在心上:到界河里挑水、烧火做饭、备料炒菜、刷锅洗碗都帮着老婆干,不摆大男子主义的架子。我老婆喜欢生闷气,不高兴时三五天不说一句话,对你不理不问,急得我气鼓鼓的。有话无人说,有理无处讲,实在憋得难受,我就一个人跑到山坳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我不愿在自己老婆面前流泪,更不愿意让她看到我内心的脆弱。 其实,我俩更多的时光是快乐的。张正美喜欢唱歌,许多老歌她都会唱。我就在家里给她办“个人演唱会”,双人床就是她的演唱舞台。虽然台下只有我一个“粉丝”,但她的演唱依然激情不减,直唱到嗓子沙哑,会唱的歌都唱完了,才告结束。 世上所有的女人都爱美,但张正美自嫁给我后,没买过化妆品,没进过美容院,也没穿过裙子。一次,我和她一起到团部参加一个广场活动,别的女人都穿得花红柳绿,打扮得时髦漂亮,就我俩从头到脚裹着一身迷彩服,好像是天外来客。我老婆一看这场面,就不走了,直往我身后躲,眼泪跟着就流了下来。我心里也难受,但又没法安慰,匆匆参加完活动就赶回了哨所。 回到哨所,张正美一声不吭,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条花裙子,这是当年我俩结婚时我给她买的。由于哨所蚊虫实在太多,裙子没法穿,就一直压在箱底。她把裙子套在身上,对着镜子端详了半天,又脱了下来,默默地换上了迷彩服。她说:“等儿子结婚时,我把这条裙子送给儿媳妇穿。”她这句无可奈何的话,让我差点掉下了眼泪。 我这个人比较内敛,平时情啊爱啊的话说不出口,但对妻子的爱那是没得说。我每次下山开会或办事,再晚都要赶回哨所,因为我知道她一个人在哨所呆着会害怕。2011年我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会议一结束,我就匆匆赶回了哨所。好多人不理解,说好不容易去趟北京,怎么也得留两天看看首都的景色,逛逛王府井大街。但那几天,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烦躁,脑海中总出现老婆一个人巡逻时步履蹒跚、随时要倒下的背影;总梦见独守哨所的妻子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夜里瑟瑟发抖、呼唤我快点回来的样子。其实,我就是个操心的命,等赶回来一看,啥事也没有。经过多年的历练,妻子早已成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优秀护边员了。 我是个不会浪漫的人,就是实实在在过日子。老婆有时候也埋怨我活得太没情调,生活提不起劲。情人节的时候,我也想买束鲜花,向妻子说一声“我爱你”,但就是做不出来,觉得假。去年“三八妇女节”我在外地开会,同屋的一个代表早晨一起床就给老婆发问候信息,祝节日快乐。这让我非常感动,想了半天,我也掏出手机,壮着胆子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老婆,节日快乐!想你的老公。” 回到哨所,我一直没好意思问妻子信息收到没有,过几天也就忘了。后来我发现妻子每天都在偷偷地摆弄手机,我感到纳闷,就问她:“是在玩游戏吧?”“不是,看短信呢!”“谁的短信?”“你的短信!”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她告诉我:“当天收到你的短信,我感动得都哭了。这可是你破天荒头一次呀,我要保存下来,没事就看看你那句肉麻的话。”她的话让我又羞愧又温暖。 张正美对我获得的每一个荣誉都很在乎,也很珍惜。每次奖章或证书拿回来,她都要亲自把证书整整齐齐摆到桌上,把奖章挂在墙上。没事的时候,就擦擦灰尘,拿起来端详半天。我常跟她说:“这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尽管她每次都摇头,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她开玩笑对我说:“我不管你拿多少奖,在家里你就是我老公,一辈子得服我管。” 要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那就是自己的儿子马翔。他1岁多离开了我们,常年跟爷爷奶奶生活,父母的爱对他就是一种奢望。一次,孩子半夜发高烧,爷爷奶奶把电话打到了哨所,问怎么办?山高路远,我们有啥办法。妻子又哭又闹,非要我陪她连夜赶回团部带孩子看病。无奈,我只好答应了!等我们冒着大雪天亮赶到团部医院时,儿子输完液已经退烧了。当时老人的一句话,差点没让我背过气去:“跑这趟就是让你们知道养儿的不容易。” 好在我儿子是个开朗、阳光、懂事的孩子。虽然在爷爷奶奶家长大,但学习的事从来没让我们操过心。那年,他靠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北屯重点中学。今年高三,他面临着人生的大考,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是尖子班的优等生,考大学应该不成问题。 24年风雨路,今日再回首。我觉得自己改变的只是容颜,不变的是那颗忠诚于祖国的心,那份坚守桑德克哨所的情。有人问过我:“你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桑德克哨所,就不觉得后悔吗?”其实每个人都有私欲、苦闷和懦弱,这就要看谁的心力强大、意志坚强,谁就拥有高的境界。我不能说自己的境界有多高,但至少面对工作和生活时,我总能以平和的心态不作攀比。我常想,桑德克哨所是艰苦,但它必须要有人守着,你不来,他不来,总得有人来。我之所以愿意长时间待在这里,是因为我把青春洒在了山水草木之间,早已变成了情感的种子,难以割舍了。 我记得,一位将军来到哨所听完我们的故事,曾欣然写下这样几句话:“一个哨所夫妻站,一道边关两人看,一份责任记在心,一段佳话留世间。”也许这就是我的人生。 (本版照片由张洪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