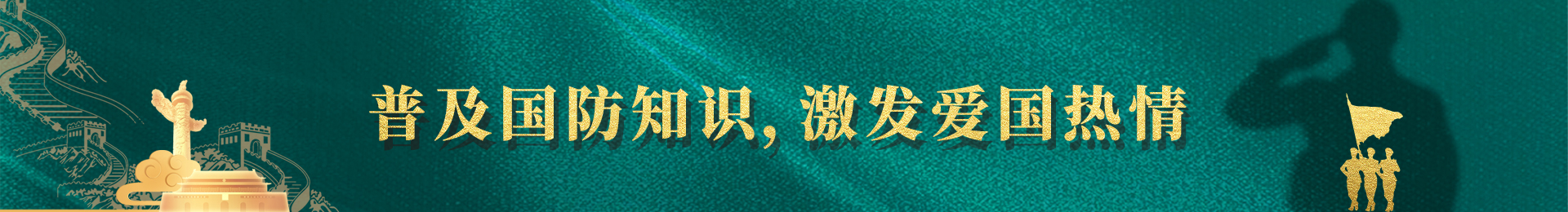协会地址:苏州市虎丘路88号

武昌起义后,各国水兵在汉口租界构筑工事。资料照片
导 读
每一个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是潜伏着许多双眼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打量,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历史因此变得更加立体、生动。
对于百年前的这场历史,已有太多的叙述和定论。但对于历史的脉络究竟是如何展开的,我们还是缺少充分的感性认知和饱满细节。
比如说,革命发生后,清廷官员是怎么想的?
在当时中国政治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列强们是如何应对的?
那些活跃的西方记者又是如何用笔和镜头来记录他们眼中的这场革命?
还有那些日后将影响中国的年轻学子们,革命发生时他们又做了些什么?
本文试图通过整理当年革命亲历者的日记、著作、回忆录等文本资料,向读者尽可能地还原一个更可读、也更接近真相的历史。
在华外国人士——
中国正书写世界头条新闻
对于辛亥革命,在华外国人士,包括公使、记者、商人,也都迅速做出了反应,留下了文字记载。他们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试图去理解这场革命。
1911年10月11日凌晨1时,武昌起义数小时后,美国驻华代办卫理就把这一消息电告国务院:“今天兵变者占领了武昌”。稍后,他又在12日午夜12时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将武昌起义定性为“自太平天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叛乱”,称赞“叛乱显得很有组织和领导”,“外国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
10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外交大臣格雷致电:
“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报告说:武昌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衙门已被焚毁。总督驻在中国巡洋舰上,泊于英国炮舰的后面。他已通知总领事说,他不能保护英租界,并已请求英王陛下船舰阻止起义军渡江前往汉口。”
在武昌起义之初,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站在了现政权清王朝一边,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采取防范、敌视态度。早在武昌起义前夕,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提醒清政府防止革命党人乘机起事。
武昌起义爆发,湖广总督瑞?逃到兵舰上后,派人与德国领事联系,声称武昌起义为义和团的复活,要求德国军舰向武昌开炮,德国领事接受了这一要求。只是由于义和团事件后,各列强间协议规定:凡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经各国之间一致同意方可实施。10月13日举行的汉口领事团会议上,德国主张协助清军镇压起义的提议,遭到法国和俄国的反对,未获通过。
此后,由于湖北军政府十分注意尊重外国人和列强的权益,未侵扰租界及侨民的安全,外国驻华机构对起义军及军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10月16日,法国驻华公使馆的斐格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说:
“新政府从一开始起便致力于维持秩序。我已报告阁下对侵害外国人和商人者科以重刑的命令,其结果是迄今为止未发生不幸事件。汉口陷落时,租界未遭到攻击。在汉阳,欧洲官商均能放心撤离。”
最终,多方权衡之下,西方列强选择了中立,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他们之所以没有像庚子年间那样大规模对中国武装干涉,并非纯然是对革命军示好的报答,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列强发现,与庚子年间反帝排洋的义和团大相径庭,辛亥革命是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清运动,并无“排外”倾向,阻挠这样的革命,维护腐朽的清王朝,并不符合列强的战略目标——让中国在一个弱而未溃的政权控制下,维持安定,以保证列强在华利益。
当驻华外交官们为中立还是武装干涉而辩论时,外国驻华记者则在一线奔波、穿梭,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兴趣。他们在一开始似乎就不看好清政府。
“武昌城并未作任何抵抗,便被革命军占领,长江上游及其他城市已和革命军将领取得一致,直接悬挂军旗。很难说是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武昌和其他上游城市,只不过是众人都默认各地易帜而已。整个过程中大约有10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其中多数是在用炸药炸开勉强关闭的城门时意外伤亡的。”
这是1911年11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报道。这篇看似对时局作客观描述的报道,隐约地传递出这么一个信息:这场革命系民心所向,以致没有爆发多少太激烈的战斗。清王朝崩溃的命运,已然注定。
“清朝危在旦夕,中国知识分子的多数皆同情革命党。很少有人顾惜这个使用太监、因循守旧、腐朽没落的朝廷。满朝文武,忧心如焚,皇上的前景有些不妙。……中国革命尽管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我坚信,革命从总体上讲是好的。”
发出这篇电讯稿的,是《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他名义上是记者,实际上是英国政府在中国的非正式代表,在满清宫廷里,他发挥着比英国驻华公使更大的影响力,也享有更大的权力。正是基于对清廷的深度了解,莫理循对中国革命前景大胆地做出了乐观的判断。
“你将会知道这个最古老而人们又最不了解的国家,正在写着世界的头条新闻。只要这个巨人烦躁地翻来翻去,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舒服地睡觉。”这是英国路透社和《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丹纳发表的报道。起义新军攻打湖广总督府的枪炮声,就是通过他的笔,把这条“头条新闻”传遍世界的。
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则从这场革命中,看到了蕴藏着的巨大商机。在《亲历中国革命:1911—1912》这本书中,他兴奋地写道:
“最近因革命引起的服饰变化,已显示出中国人更换服装的巨大需求。由于剪掉了辫子,人们抛弃了曾经非常时髦的小而圆的满族式帽子;立即产生了对外国帽子的需求,商业机会也被创造出来了。进入这个国家,你会发现各种式样与质地的外国帽子——毡帽、软帽等等,销量成百上千,这都得有人供货。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制造这些帽子,对她来说,它们是非常新颖的东西,不得不仰仗外国。日本注意到这一点,她抓住了商机,在两个月内,她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的帽子市场,这仅是一个例子;还能举出更多事例,显示商业机会的快速到来。 ”
在看到革命是历史潮流,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一些外国人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次革命的局限性。
作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英国人濮兰德曾被清廷授予四品官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十分熟稔。民国建立后,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实质性的改变。1912年12月份,在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时,他说:
“现在的中华民国并不是美国人理解的真正的共和国,有效率的共和政体并未建立起来。……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制度根本就没有最起码、最基本的理解。……这个所谓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他正在按照慈禧太后的方式,而不是美国人所熟知的共和体制来管理政府。换句话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独裁统治,来取代刚刚推翻的独裁统治。”
濮兰德认为,中国有句谚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非常贴切地隐喻了当前的形势。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后,中国人的内心并未因此发生任何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没有步调一致的起义,大多数人的心中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和吁求。“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无革命性的群体。”
濮兰德的观点虽然不无偏激之处,却也一针见血。
年轻精英学子——
被革命的浪花溅湿了衣裳
容易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学子们,总是对时局表现出独特的热情。在1911年这场大革命中,许多人或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受到了革命氛围的熏陶,被革命的浪花溅湿了衣裳。
1911年10月13日,武昌起义后开出的第一条船抵达长沙,带来了湖北革命的确切消息。正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毛泽东,在听到革命党人激动人心的演讲后,决定投笔从戎,而且目标明确:到武汉去,参加湖北革命军。
在启程北行前,他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于是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那天,正好是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事的10月22日。在借鞋的途中,毛泽东目睹了大批起义士兵开到街上的场面。
25年后的一天,在延安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他那天“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
没有太残酷的战斗,长沙起事顺利得像是一场和平交接。长沙革命成功,当兵何必舍近而求远?于是,毛泽东直接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列兵。《毛泽东自传》一书中,对他入伍后的生活有这样的记述:
“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不过,已经多于目下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
尽管这段行伍生涯很短暂,但对毛泽东而言,无疑是一次革命思想的启蒙。
革命风潮很快席卷神州。在处于清王朝心脏地带的北京城,日后的国学大师吴宓,此时正在清华学堂读书,他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视角,逐日记载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京城引起的巨大震荡,其中包括社会的动乱、统治者的昏庸、人心的向背、战局的进展、学校受到的波及等,体现了一个青年学子的忧患意识。
1911年10月30日,当学校老师谈到希望清政府通过武昌起义吸取教训,作适当政治改革时,他却对此表示怀疑:
“午后,监督唐演说今日所下五道诏谕,言自此乱事可平,诸生在此亦无忧患矣。而国文教员杨亦言,此后政府或能稍行改良政治,革命之事或将由此而止。果政治上能得少许进步,然亦以多人之血易之而来者,实则其果能改良与否,亦未确定。”
吴宓的老师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头上,而年轻的吴宓却表示怀疑。而事后局势的发展,正印证了吴宓的判断。
当苏州光复时,17岁的叶圣陶正在苏州草桥中学就读。他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欢庆,到巡抚衙门瞻仰光复后的都督府,看到府上高悬一面“兴汉安民”的白旗。目睹革命新气象,他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道:“上头不再有皇帝,谁都是中国的主人。”
为表示自己坚决赞同革命的态度,叶圣陶很快剪去了辫子。在日记中,他这样描述:“‘磕榻’一声,豚尾之嘲已解,更徐徐修整,令之等长。对镜自照,已不出家僧矣。而种种举止行动得以便捷,则我生自今日始也。”
叶圣陶此时颇为活跃,还于1911年11月21日在刚创刊不久的《大汉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欢呼苏州光复,认为“改革尤须改革心”,要通过报刊宣传“张我大汉魂”。在日记中,他阐明了自己这么做的动机:“杞人之忧当不见屏于大文豪之前,实以张目张耳即触不满意事,故毅然呼号也。”
1911年,瞿秋白是常州中学堂的一名勤奋上进的学子。辛亥革命爆发后,一直关心时政、思想上支持革命的瞿秋白,动手把辫子剪下,拎着它欢欣地对母亲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这是少年瞿秋白对当时社会变化的体验之词。
与当时许多人一样,当看到象征着五族共和的民国五色旗飘扬在丽日晴空之下时,瞿秋白也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不过,在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后,时局却变得有些让瞿秋白看不明白了,他对这场革命有些怀疑。
1912年10月10日,正当常州的居民和各机关学校都在张灯结彩,庆祝“双十节”时,瞿秋白却制了一个白灯笼,用毛笔在上面写下了两个大字“国丧”,然后高挂在宗祠侧门上,以此表达他对民国的失望。此后,他走上了探索救国真理的道路,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清廷王公大臣——
没人愿做清王朝的殉葬品
清朝的官僚阶层一直以来,都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部件。可在武昌起义后,他们的表现令清廷万分失望。
1911年10月10日晚,在起义新军的隆隆炮声中,湖广总督瑞?命令手下炸开总督署后院围墙,仓皇逃到停泊在长江口的“楚豫”号军舰上了。
不过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把情况想得太坏。他的第一判断,这只是一场士兵哗变。第二天,瑞?向内阁发电说:
“此次匪党作乱,本已破获,讵有新军应匪,构此奇变……去年,瑞?到任,适值广东兵变之后,瑞?即欲将鄂中新军严加清查,以别良莠。嗣经张彪力保,瑞?亦以此军为张之洞所练,张彪又系原练之人,乃妨(仿)萧规曹随,殊不料其竟与匪通也。”
在这份电稿中,瑞?在报告武昌起事经过后,着重为自己放弃省城开脱责任:近因归之于新军统领张彪统兵无能,远因则归之于前任总督张之洞练兵“均为匪用”,并吁请清廷立即派兵“来鄂剿办,俾得迅速剿灭”。
瑞?这份电报的字里行间,折射的是典型的晚清官场风格。官员们习惯了当“太平官”,一旦遇事,第一反应不是如何有效处置,而是推诿责任,上交难题。
不单瑞?,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的军政要员几乎犹如丧家之犬,或逃,或降,或避。提法使马吉樟一闻新军起义,不知如何是好,派人打听投降办法,又无结果,于是正其衣冠,危坐大堂之上,等革命军来纳降。谁知从11日凌晨坐到中午,革命军也不找他,他于是从容出走。
武昌发难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震惊,迅速派兵前往平叛。这年头,朝廷上下到处不平静,可到最后不还是都挺过来了吗?在当权者看来,只要拳头硬起来,武昌闹事的新军跳不了几天。10月12日,关于镇压武昌起义的“上谕”说:
“着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严饬萨镇冰督率前进……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
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满洲正白旗人、陆军大臣荫昌自北京车站乘专列奔赴前线。曾跟随李鸿章办洋务多年、时任邮传部大臣盛怀宣前来送行,并交给荫昌一张地图,请他下令前线军官在进攻汉阳时,要保护好钢铁厂,少受损失,即赏银10万元,由他本人负责照交。荫昌笑答,你就准备钱吧。
此刻的荫昌对战局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还未开打,但败局已定的仗。不过,帝国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物。
被清廷赋闲在家的袁世凯,是在10月11日接到武昌兵变消息的。那天,恰好是他的生日,他属下的一帮文武官员赵秉钧、段芝贵等齐聚洹上村为他祝寿。得知兵变消息后,袁世凯立刻下令停止寿宴,面对相顾失色的宾客,他只说了一句话:“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袁世凯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是因为他一直对时局非常关注,与朝野名流保持密切交往,深知当时民心思变。
当前线的战局并不如意,且南方省份纷纷开始响应独立时,清廷才意识到,局面失控了,这次大清国可能真的要栽倒了!在这个关乎存亡的危急时刻,北京城里的清廷权贵们,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誓死捍卫大清朝的决心和打算来。相反,京城里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出现了挤兑潮,王公大臣也加入其中。
10月30日,御史史履晋在奏折中忧虑地说:“京师银根奇紧,银行、银号、炉房已倒闭十余家,大清储蓄两银行又被拥挤。……人心摇动。”
王公大臣们带头挤兑,带头出逃。天津的租界,此时成为达官贵人最理想的避难地。租界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商机,旅馆、饭店纷纷涨价。
10月30日这天,翰林徐兆玮在日记中写道:“继至车站,见出京者纷纷,比前数日更多。……今日谣言甚盛,并云革命党人有入都消息,以致城内外纷纷迁至外城。人心涣散,一至于此,真可叹也!” 11月1日,徐兆玮买到了头等车票,上了车却无容足之地,一路站到天津,只能叹息“苦矣”!富甲天下的盛怀宣早已亡命日本。他的次女婿11月9日也仓促出京,乘轮船南下到上海。
那些尚留在京城的官员们,也是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想方设法寻求外国人的保护,有的干脆跑到使馆区外国人开的饭店,因为那儿安全。翰林恽毓鼎在11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使馆街有六国饭店,朝贵恃有外国人也,群赁居之。每屋一间住十余人,每人每日收租洋九元,……每餐仅饭一筒,盐煮白菜一器而已。……至有宿于廊下者。偷生受辱,一至于此。”
大难临头,京官们作鸟兽散,地方的督抚大员们心里也是明白得很,于是各作各的打算。江苏巡抚程德全赶起时髦,摇身一变成为了江苏都督,背叛了此前效忠的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和革命党人达成默契,弃城而走,广州和平光复。这个时候,没人愿意做清王朝的殉葬品。
清王朝不单失去了民心,连官心也失去了。恽毓鼎在日记中感叹:“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麋集,患难则兽散。”
清王朝的覆亡,已成定局。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颁布。这一天,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曾经的摄政王载沣在日记中写道:“即日亥刻停书日记。”他多年记日记的习惯,至此戛然而止。几天后,他刻了一枚闲章,曰“天许作闲人”。1951年,68岁的载沣在北京辞世。周恩来评价他时说,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载沣其实是个明白人,他早就洞悉清廷大势已去,索性做一个散淡的人。